2017年,杭州一对老年夫妇发起“抱团养老”,招募愿意同住的老人。超过100对老人报名,4对入选。一年后,有人离开,有人补位。
这些老人以“抱团”作为人生最后一站的中转。他们身体老去、子女缺席,但在这些刻板的印象之外,他们同样需要处理与同辈相处的纷争、自身纠结的情欲,他们强烈地渴望存在感,并努力争夺群体话语权,这些欲望并不因为年老而逐步消退。
我们终将衰老。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,才能更好地理解养老意味着什么,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。
①
周年的句号
一年前,69岁的叶吉华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消息,杭州一对老人想在自己家弄“抱团养老”,招聘4对60岁左右的老年夫妇,同吃同住。他和妻子报名,随后被选中。一年后的这天,他们却决定离开。
司机给车厢蒙上了橙色的塑料布,又把凉椅推到车尾,卡在杂物中间。妻子坐在前头,叶吉华扶正自己的鸭舌帽和墨镜,把30块的单肩包扯到身后,托着180斤的身体,跨一脚,扶一把,成功登上自己的座驾,没有蹭脏白T恤。
卡车轰隆隆发动,从别墅二楼下来的最后一对“原始股”夫妇挥挥手,“别走交警多的地方,小心被抓!”
叶吉华曾满怀希望。他最初被通知,“有一百多对报名,特火爆。”等待半个月,一对拥有资格但放弃的夫妻给他电话。他和妻子坐了两个小时公交,赶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港东村面试,他当时在痛风,一步一瘸,跳着脚。
获得房主的认可后,叶吉华电话喊来小舅子的七座商务车,拉了四趟,把所有家当都拉来,又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说,要在这儿住上个三四年,等夫妻里谁不行了,再进养老院。
离开时,他更为坚定,他对我说,“我们不是曹操,得赶紧走,不像有人就一定要待在这儿,跟他们扛。”
“他们”是指房主夫妇和正在三楼搬房间的蒋一纯。蒋一纯说,“离开的人就是个句号,管他做啥呢?”
[url=]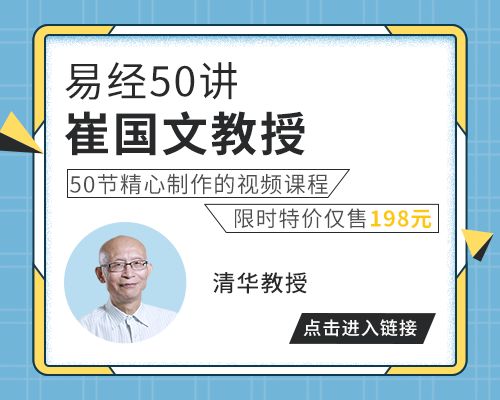 [/url]
[/url] ②
衰老是身体零件越来越少
叶吉华走的前一天,一对夫妇不顾大雨,按照媒体上的几条线索,跟着公交车找到村里,想要面试。男的79岁,女的74岁,与房主夫妇同龄。房主出去看病,他们在客厅等了3个小时,叶吉华看他们诚恳,和他当初一样,“真心想来”,私下支招,“你们就扒着大姐,她不答应你们不走,一定能成。”
大家尊称房主妻子一声“大姐”。大姐是“抱团养老”的发起人。2016年,丈夫患了膀胱癌,手术后整天窝在沙发里叹气。三层别墅两人住,太空荡,吃饭也常用速冻饺子对付。公路对面的村庄面临拆迁,夫妇俩连麻将牌友都找不到。她联系到当地媒体,登了一则“招租启事”:想找几对老人抱团养老,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,有生活自理能力,经济上不能太计较,另外,只能招家住杭州的,周日要把房子腾出来。
2017年5月,叶吉华刷微信的时候看到了启事,他马上留言。叶吉华8年前退休,不再背着金项链闯苏北干销售。几十年前一起去黑龙江兵团插队的朋友,在山上开赌局,打斗地主,200元起,他只看看,不敢打,“一打四五千,就是一个月的退休金。”他到处报老年旅行团,每去一个地方,他都要在朋友圈发9张照片,留言一句,“谢谢亲们关注!”
叶吉华的妻子俞右今年也69岁,以前是印刷厂工人。衰老是逐步减少一些东西。她身体的零部件越来越少,前几年得甲状腺钙化,切掉。子宫肌瘤,切掉。又患乳腺癌,再切掉一边***。叶吉华陪着她在肿瘤医院做化疗,每个月要打长长的黄色药剂推针,药水滴在皮肤上,会腐烂和起泡。
痊愈后,俞右闷在家里打游戏。电脑屏幕小,眼睛看着吃力,得连着电视才行。《魔兽》、《诛仙》、《奇迹》,她不打打杀杀,只挂机杀时间、捡装备,把号练到满级,转手卖给年轻人——一共卖了好几千。她最喜欢坐着《奇迹》里的一条龙,在服务区里跑来跑去,金灿灿的很舒服。
来到港东村,有人陪着一起搓麻将、摘毛豆,俞右把游戏戒掉了。她找回了几十年前下乡插队和工厂生活的集体感。住二楼的老人金珏从楼梯上摔下骨折,每天要洗澡,她帮对方缠保鲜膜,又擦又洗,弄了两个月。后来她头晕,抬手都没力,金珏赶紧让丈夫拨打120,夜里陪她去医院。


▲叶吉华
今年1月,一对夫妻离开,66岁的老人蒋一纯补位。他常戴一顶帽子,穿薄荷绿衬衫、白西裤、白皮鞋,Coach和Calvin Klein的皮包轮着挎。他给记者看三十多顶五颜六色的贝雷帽穿在一条绳上的图片,记者回去写,“戴贝雷帽的长发活力老人,很有港星范儿。”
只有一个人待在房间时,蒋一纯才会摘掉帽子,露出地中海,脑袋顶还剩几根绒绒的毛。
2012年,他退休,领了一张敬老卡。第一次拿新卡坐地铁,刷卡时,他没想到闸机会叫,“老——年——卡”。听到尖尖的女声,他难为情,背过身体走进站。蒋一纯曾做过城市宣传片编导,央视给编外人员发三个月的政府救助金,他也不要,人事是他大学同学,问他怎么不拿,他反问,这有什么好拿的?
他闲不住,接下儿子的Ford保姆车,65岁考驾照,他硬是一把过。教练骂其他学员,“老爷爷都比你们开得好!”
但85岁的丈母娘骨折了,他和妻子下定决心把老人送进疗养医院。我和蒋一纯一起去看望,她坐在轮椅上,护工正更换贴着病床的纸尿裤,被换下来的皱成一团。隔壁床的老人95岁,戴着呼吸机,“嘶嘶”地呼气。
蒋一纯妻子推着轮椅,打算绕7楼走廊逛一圈。老人家看到另外两个坐着轮椅在走廊透气的老人,很高兴。她想介绍我,但是舌头中过风,含糊不清地咿咿呀呀,刚说一句话,口水流出来,她没顾得上擦,继续说。
蒋一纯坐了20分钟,很快就走了,他一周来几次,每次都不超过半小时。去年他和妻子陪丈母娘吃年夜饭,看着一个老人过世后被推出去,他没法忍受。
叶吉华也去看过养老院,全封闭管理,出去要打请假条,叶吉华感到好奇,一问,几年前,一个失智老人走出门外,再也没有回来,也没人索赔,只有民警的档案还留一个最后的名字。他赶紧拉上妻子要走,“一个人,就被当成一件事给处理掉了。”
[url=] [/url]
[/url] ③
“不靠子女,靠自己”
别墅里的老人多是夫妻加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,叶吉华摆手,“想开了,我们是不靠子女养老的第一代。”参与抱团养老,也是最终走进养老院前的一场中转。唯一一个独身老人说,来这儿之前,她每天用保鲜盒装着女儿家的剩菜泡证券所,在这儿至少吃饭有人陪,菜多,还能转圆桌。
离开抱团养老的家时,叶吉华打电话给儿子,来帮我们吧。儿子说,刚从日本出差回国,不来。
儿子在《奔跑吧兄弟》剧组,全世界地跑,有时候给他发,这是和邓超的合影、和江一燕的合影,叶吉华把照片存入收藏夹,拿给我看,又指着蔡少芬,“这个好像是香港的。”
叶吉华和儿子三个多月没见了。还没搬来港东村时,每个月儿子最多来家里一次,他烧儿子最爱吃的大排,但6点开饭,儿子5点半才到,7点一过就走。原本的房子给了儿子,嫌小,租了出去。儿媳很强势,坚持丁克。有次俞右让她别喝酒,被摆了一天的脸色。俞右私下和他商量,“别和他们一块,我们自己住吧。”
叶吉华总说,自己还有3600天,一定要去巴厘岛,“我儿子之前去了两次,说那边景色特别好。”我问他杭州哪家饭店好吃,他带我去儿子两年前和他吃的“弄堂里”,一家人均70元的本地菜。他很久没来,我们到的时候,门店在装修,到处扬着白灰。
送走叶吉华夫妇,其他人回到各自房间。大姐来到厨房,把一早藏在电饭煲里的烧鸭拿出来,又剖开了黄鳝,她的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、孙女外孙女都要来,每周日一起吃晚饭。
最初招人,房主设条件,“儿女最好在杭州,每周日晚上要回家相聚。”但没人能像他们儿女这样规律“探班”。金珏在房间煮饺子,她拿给我看外孙女三四年前拍的卡片艺术照,上面一层保护膜皱皱的,一直舍不得撕。
央视来采访,住二楼南侧的高林林因摄像机拍她而大发雷霆,疯狂甩头指责的背影被播出了。后来又有媒体扛着摄像机来采访,她把房门一关,还要在饭桌上特地嘱咐,相机没开吧?
她没向大家解释,母亲并不知道自己来这里。母亲今年76岁,也想一起来抱团养老,但母亲“缠人”,每天晚上12点还会来敲门。她撒了谎,告诉母亲,自己是搬到厂房里去了,别来看我。
她又提起儿子,不按时吃饭睡觉,居然还不按时结婚,30岁打光棍,真烦。儿子晚上12点半还在打游戏,她坐在客厅沙发,等着。等不住了,进门把儿子电脑关掉。儿子学聪明了,反锁房门,高林林就趴在地上看门缝,电脑屏幕一闪一闪,她敲门,儿子不开。她把总闸一拉,儿子甩门,用杭州话大吼,你做啥了,发疯啊?能不能把我当隔壁家的小孩啊?
丈夫想劝,只说了句,你别让你妈生气了,儿子不理,眼睛瞪着。又劝高林林,别和儿子闹了,这么大了随他去。高林林一哼,“要么眼睛不看到,要么我死掉。”
等在报纸上看到抱团养老的消息,她想,算了,房子留给儿子,我走。搬过来后,她趁每周日房东团聚回家,但儿子常常不在,还留一个臭苹果在角落,等她收拾。
最追求热闹的蒋一纯也说,“儿不管爸,爷不管孙。”儿子做外贸,每次去国外出差都会带奢侈品,妻子有PRADA的墨镜、COACH的皮包、迪拜买来的宝石项链,仍难和儿子见上一面。狗是人到晚年时重要的伙伴,蒋一纯养了只雪橇杂交犬,叫“格格”,6岁,皮毛光滑,总摇着尾巴。他不许格格和公狗交配,也没有给它做绝育手术。
▲蒋一纯
房主也有两只狗,种类未知。老的叫“宝宝”,守在前门,“宝宝”和无名氏生的孩子,叫“贝贝”,锁在后院。房主不管狗,从不允许它们进入房内,喂饭的任务交给高林林的丈夫小张。他每周煮一次狗饭,狗吃的米一元一斤,人吃的三元一斤,煮好了就冻在冰箱,每天铲出一块,拌点儿剩肉,热水一冲。
妻子去日本旅游,房主网开一面,允许蒋一纯把狗带进别墅,走哪儿跟哪儿。他给格格喂火腿肠,一截一截丢着喂,哄着吃,旁边的狗粮没怎么动。
宝宝又不知和哪家的狗交配了,摸肚子能感到很快的心跳。小张说,“宝宝怀孕的孩子得扔,夏天生的狗不好养。”
④
纠结的情欲
对外,叶吉华总说,害怕妻子犯病,港东村离市区太远,连唯一的卫生院都给拆掉了,必须得走。
和叶吉华一起被选中的四对夫妻,有两对早已离开,一对待了两个月,家里父亲出事,要赶回去照顾。另一对退休前是医生,但男的中过风,脑子里有斑块,左手总在抖,有次没端稳饭碗,菜撒一地,有人在饭桌上笑出声,医生铁着脸,第二天就打包好了行李。
轮到叶吉华和俞右,临行这天,俞右打包整整一纸箱的药物,叶吉华坐在旁边笑,“你就是似懂非懂,最可怕。”
房间里有两张一米二的小床,铺着格子花纹的床单,俞右一翻,把这层皮扯了下来。刚来的时候,这里只有一张大床,俞右找到大姐说,最好换一下。
退休后,两人就已经分房。叶吉华睡觉要关门,俞右开着门,分房都清静。他们住在母亲过继的房子,两间房装着电铃,如果有紧急情况,这边拉下,隔壁就会响起。
欲望依然存在,但看到戴着义乳的妻子,叶吉华没什么想法,只天天出去走路,要对着微信运动走一万步。“找个老太太,也实在没心情,难不成去找小姑娘吗?走一走就消耗掉了。”
他身体衰退不明显,只有三颗牙晃得厉害,干脆拔掉。看到房东复诊膀胱癌回来,他私下对我说——很多男人老了都前列腺肥大,小便滴滴答答的,尿不干净,他还可以。
“每个人(有需要)的时间段不一样,5月搬出去的一对,大姐就觉得他们不正经。”叶吉华去看望骨折的老范,老范之前经商,很有钱,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,却把家送没了,成了单身汉。和他一起住进来的女人,自己也还有家庭。大姐认为这有损抱团养老的形象,“你们住这儿可以,但必须得有手续。”
叶吉华几次去到老范住的疗养院,发现那个女人也没来照顾,只留下他一个人。叶吉华说,“这个年纪的夫妻,感情早磨完了。如果没有经济利益,很容易分开的。”
但总有需要另一半的时候。去年元旦,俞右在小区广场跳广场舞,突然感觉站不住,蹲下来,不行,坐下来也不行,心脏像打鼓一样,要跳出来了。她给叶吉华打电话,胖子快来,扶我一下。叶吉华穿着裤衩就从家里冲出去,手机没带,医保卡也没带。
俞右在港东村犯病时,叶吉华正在参加泰国老年旅行团,第一次出国,他舍不得开国际漫游。等回来,他才知道俞右的心脏又出了毛病,想起来后怕,不敢和妻子分房了,还是得分床。
高林林和丈夫是屋里唯一没有分床的夫妻。她最小,53岁,去年体检,她看着自己颈动脉里漂浮的毛状物,感到害怕,把柜子里塞满鱼油、大豆磷脂、牛初乳、钙镁片。月经很久不来,她去看医生,医生说,是时候了。又问她,要是想服药缓个两三年也行,很多女人为了维持青春,都会吃激素的。
但她一听到会增加乳腺癌和宫颈癌的风险,连忙摇头。停经一年,身体就有了巨大改变,她骨质疏松、发根变白,鼻根附近开始长斑,夜晚常觉得燥热,每当丈夫“想要”,她烦得很。
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脾气,饭桌上,她会把骨头咬得粉碎,炫耀似地对蒋一纯说一句——“还是我的牙齿好吧?”
▲蒋一纯
蒋一纯回头又和我说,“别去采访那个53岁的,脾气太差。”53岁的高林林曾和他说起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,一次在电影院,有个男人和她一起坐,把手搭过来,她直接拧起对方胳膊上的皮。
另一次是走在路上,陌生男人对她吹了声口哨,她脱下高跟鞋,对着那个男人的脑袋拼命地敲。
边说着,蒋一纯边演示,把自己胳膊上的皮揪成漩涡,老年斑都扯变形了。“我说句不好听的,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,打扮不就是给异性看的吗?真正老成树干了,谁看你呢?”
⑤
钱是个敏感问题
今年年初开始,三十多家媒体和六七家大学教授陆续来采访调研,考察首例“成功”的抱团养老的可复制性。一茬茬的摄像机摆着,针对动机,房主起初回答“患癌之后感到孤独”,后来接受采访多了,他说,“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,抱团养老还是个新鲜事物,但是国外老早就有了!”
房客们则流利背出几个短句——“空气好、房租便宜、菜好吃、有人打麻将”,每次算完账,都要提到挂在门口的褐色皮包,菜钱在里头,再对镜头说一句,“我们这儿很公平!”
大姐之前是化工厂厂长,管理经验丰富,极力推行经济民主,朝南房间月租金1500元,其他朝向1100元,房租用于支付聘请的厨师、园丁、保洁阿姨工资。饭钱按顿数算,早餐一画,中餐晚餐两画,一天一个正字,叶吉华和俞右在这儿开销一月每人不过两三千,比养老院划算。
但钱总是一个敏感问题,别墅里的大多纷争均与此有关。有人去隔壁镇买菜,要报销三元公交费,蒋一纯不乐意,“那我开车去买菜的剐蹭要一两千,给报销吗?”
冬天,俞右心脏遇冷不舒服,空调太奢侈,叶吉华买来烤火器,夜尿起来开一开,其他人看到,说他们在***,要单独放个电表才行。秋天李子熟了,叶吉华请园丁摘三斤,想之后再付钱。大姐撇下嘴来,“这是给我儿子吃的。”
他们很少有大的集体活动,吃完晚饭,大家出去散步半小时。下雨天,就排队围着客厅的沙发转圈。散完步,大家关上各自的房门,一天又过去了。他们很少聊起过去的经历,住在二楼的周益民宁愿一个人,对着手机上的AI程序问天气。
四人麻将是每天固定的活动。叶吉华告诉我,俞右有次打麻将赢了一两百,大姐背后说她作弊,“耍阴招”。大姐又说,叶吉华自己不打牌,是因为刚搬进来时玩三人组队的扑克,才输几把,就粗声粗气地要“指导”她该怎么出牌。
[url=] [/url]
[/url] 老人们各自的家境不同。蒋一纯在杭州有两套房,“待在自己家舒服多了。如果是在社会上,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是不会打交道的。比如毛毛(叶吉华小名),为了省钱坐两个小时公交去原来的社区理发,8块钱。那他坐公交不就花掉4块了吗?还有二楼那女的,房子刚被拆迁吧?”
但蒋一纯又翻开文件夹,一个个滑过去每一张报纸上抱团养老的标题,用手指按住“相聚容易相处难”,“这标题是所有报道里最差的一个,太夸张了,我们相处有什么难的呢?”
⑥
争夺摄像机
面对摄像机的关注,老人们的态度开始有了分歧。5月,瓶窑镇组织健康养老餐活动,蒋一纯上台,吐字缓慢,“我作为抱团养老的代表,感谢大家关心,希望镇政府和村委能给我们更大的帮助和支持。”说完他挺得意,“这话他们说得出来吗?只有我能讲。”
▲蒋一纯和房主的狗“贝贝”
叶吉华对我说,他当时坐在底下,心想,你才住4个月,平常洗碗你不干,记者来,你才在,你凭什么代表我们?
吃晚饭时,叶吉华没忍住,对蒋一纯说,“50岁以前不出名,现在要出名也晚了!”蒋一纯没吭声。吃完他才说,“如果不是我,有些人一辈子也上不了电视,还是中央台”。一听这句话,他和另两对夫妻撂下筷子,“我们才不想上电视,吵又吵死,烦也烦死,连水电费都没给我们解决。”
一位来调研的专家发私信给叶吉华,“老蒋的目的好像和你们不太一样。”他觉得专家看事情一针见血,回复一句,“恐怕日后要变味儿!”
月底,叶吉华夫妇去俞右弟弟家做客,发现对方正准备把自家房屋出租。自麻将事件和“***”事件后,叶吉华夫妇便开始重新物色养老院,始终没定下来。俞右拉着叶吉华,“干脆就把弟弟的房子租下来,马上搬。”和弟弟商量完,她发微信给金珏,回来会晚些,帮忙剩一点儿菜饭。金珏饭后散完步,俞右才回到港东村,对她说,今天去看房,定下了,得搬。金珏想劝,看对方神色坚决,只说,“那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!”
过了一会儿,大姐回来。叶吉华夫妇提起搬家,其他人在旁边听着,不相信。第二天吃饭再说,大家才相信。问他们理由,叶吉华回答,身体不好就医难,正好有房便想搬了!
叶吉华想起协议书上要“提前一月告知”,所以留到了6月。记者源源不断地来,叶吉华和俞右不耐烦。蒋一纯却越来越兴奋,抱团养老亲历记从每天一句话增加到一页纸,他开始强调,“我要把这个做成事业。”
他为所有采访过的媒体拉了一个群,他是群主,在里头跟进新的采访内容,29个记者待着,不吭声。群名叫“左右逢源”,问他为什么这么取名,他笑,“这样做人不好吗?”
6月22日,他去杭州电视台录养老模式探讨的圆桌会议,他提前写了8页草稿,又编了几个排比,“政府要资助,社会要公助,企业要捐助,个人要自助!”
地铁上,他一直碎碎念着提纲。房主和大姐坐在旁边,一声不吭。房主衬衫扣子松了两个,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,蒋一纯让他扣上,注意形象。
前一晚,我和老人们一起饭后散步。我问大姐,明天什么时候去录制,大姐含含糊糊,“还没定”。我身旁的高林林原本在夸刚摘下的黄瓜好鲜,突然不说话了,走进路边的阴影里。后来她向我解释,就在一小时前,大姐才告诉她,明天是去看孙女,不回来吃午饭了。她没想到大姐准备瞒着她去录制节目。
“我和毛毛他们,原来都以为只是老蒋喜欢出风头,现在发现房主和他是一起的,把我们当傻子弄。”高林林说。
此前,新加坡和香港分别有媒体来采访,他们外出避开,只剩下房主和蒋一纯招待。蒋一纯有了名人的信心,巴拿马的朋友看到新加坡《海峡时报》的报道,特地打电话过来——“兄弟,报纸上的蒋一纯是你吗?”
[url=] [/url]
[/url] ⑦
“有名才有利”
7月3日,抱团养老一周年,叶吉华和俞右回来,大家一起去了农家乐。他推荐的那对高龄夫妇也来了,他们获得试住资格,搬进叶吉华原来的房间。
▲蒋一纯和房主
所有人入座,服务员端上卤鸭、烧鸡、螃蟹、鲈鱼,高林林拽着螃蟹腿拼命咬。在场还有四家媒体,架着摄像机,房主扯着嗓子发言,“今天我们抱团养老一周年,目的达到了。老年人住在一起,我们觉得很快乐!在老蒋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,让全中国人民看到我们抱团养老的好处!”
镜头转向叶吉华,他却切换成杭州话,简单说了两句,“只强调一点,所有的事情大家共同做。”
轮到蒋一纯,他有些激动,手伸起,“余杭哪个地方会有三十多个媒体来?这说明人家看得起,我们是正能量!政府部门的支持,我们正在争取!”
以往拒绝在媒体上露面的高林林策划好了,要在这时说出来。“凭什么这么多家媒体来?你之前说,有名才有利。我们本来就想安安静静来养老,没想过什么名利,有人好像变味儿了。”
上午出发前,高林林希望我能拍下一张图片。图上写着房东抱团养老前后的收入对比,“他们对媒体说这是公益,实际上是赚钱的。”她还对我说,有两次她刚跟金珏说完悄悄话,去上厕所,发现房主就站在门外。她当面说房主,“你干脆定个规矩,房客之间不准说话超过十分钟!”
蒋一纯更激动了,“我们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媒体来,在场四家哪家是我们请来的?”其他人稳住老蒋,林林不说话,但她又伸出手比画,“没有我,你们怎么上中央电视台。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?”
新来的夫妇放下碗,想插一句,但总不得空。终于赶上趟,“今天是欢送和欢迎的日子,大家都说点儿烧香念佛的话。”
表达意见的人数达到顶峰,包厢充斥着男人和女人的尖叫,听不清谁是谁。叶吉华和大姐对骂,大姐说,再说就走。叶吉华反问,实事求是,暴露给媒体不正常吗?高林林和蒋一纯都站了起来。
金珏的丈夫周益民从不在饭桌上说话。平日里,他像个幽灵,每天吃完饭,他一声不吭地洗碗、上楼,只有一天两个快递上门时才有存在感。
今天餐桌上,周益民一反常态,对着蒋一纯大吼两句,“4月的餐数记账表,你一共才18画,我们一天一个正字就5画,你数数你一个月才来几天?”
20分钟过后,包厢终于安静下来,只有摄像记者搬着镜头跳来跳去。蒋一纯垮着脸,撑着说,“这很正常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。”新来的夫妇举起王老吉,其他人附和,大姐最后圆回来——正好好久没开民主圆桌会了。
[url=] [/url]
[/url] ⑧
离开
午饭结束,叶吉华夫妇、金珏夫妇和高林林先坐着面包车回来。车上,金珏复盘起桌上的吵架,呸呸两声。高林林像是获得了胜利,“还什么助什么助,那话反正我是说不来。今天他终于露出本来面目!”
进门的时候,宝宝叼着鲜花,凑近每人的脚跟闻一下,高林林笑开了,“你看,我们都是好人哦!”叶吉华和俞右坐了一会儿,不顾太阳暴晒离开。蒋一纯随后回来,上到三楼,关上了房门。


▲房主和新入住的夫妇
高林林的丈夫小张又缺席了这次纷争。蒋一纯带着狗走的那天,大姐和金珏随后又起冲突,两人的吵架声穿透三层楼。梅雨来了,餐厅迅速变得晦暗无光。小张光着膀子,桌上摆了八道菜,餐桌空无一人。他拿着一罐黑啤,摊开一张报纸,等待争吵的结束,“他们,就是没事做。”
他走到后院,拿竹条扫帚从头到脚地给脱毛的贝贝挠了几下,贝贝嘴里直“呼呼”。铁链紧紧拴住,贝贝脖子被勒脱了一圈毛,身上沾满了灰尘,它跳来跳去,铁链撞击地板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应采访对象要求,叶吉华、俞右、高林林为化名
[url=] [/u
[/u